乾隆时代受到追棒的原因在于大家对于经济的看法,对钱的盲目崇拜,是羡慕那个时代有钱。人们很肤浅地将钱多与国力强混为一谈。
清朝第四任皇帝——乾隆皇帝弘历,1709年出生,于雍正十三年九月(1735年)登基,到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8年)去世,一共当了60年零3个月的皇帝和3年零3天的太上皇帝,足足执政63年,做了很多事情。人们都说,中国的18世纪是乾隆的世纪,那个时代是至今被很多人称为“盛世”的时代。
应该说,雍正皇帝留给乾隆的是一个边疆比较稳定、没有内患、国库充盈的国家,同时善于反省的乾隆本人在对国家的治理上也是殚精竭虑。后人们评价,伟大的乾隆不仅经常通过免除天下钱粮来体恤百姓,还力遏贪风,在位期间指挥编撰了《四库全书》并大兴纯粹的汉学,对外政策也是以宽为主,刚柔并济。
但今天,我们看到在乾隆末年时期,清王朝之前的稳定不复存在,平定60年的苗疆地区兵戈又起,各方动乱令朝廷应接不暇,晚年乾隆一直处在苦恼之中:到底哪里做错了?为什么大清此刻连小小的安南和缅甸都打不过?什么原因使中国在他的一生中变化如此之大?乾隆带着疑问过世之后,中国开始走进黑暗的19世纪,直到内忧外患将清王朝彻底覆灭。
很多学者认为,19世纪中国的悲惨正是源于18世纪的乾隆时代。那么,清亡国真是亡于乾隆朝?60年乾隆“盛世”于大清究竟是福是祸?
将乾隆朝作为盛世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当时生活物资的丰富。
与当时刚刚兴起的西方工业社会比较,乾隆时期自然经济可谓鼎盛。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份额32%,居世界首位,比例相当于今天的美国,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共占17%,五国的GDP只有中国的一半稍多。重商主义的影响下,当时的西方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18世纪时,一度占英国出口总额90%的呢绒类西方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却并不畅销,而英国平均每人每年要消费1磅茶叶,为此流失了大量白银,却无法停止从中国进口茶叶。同时,西方还从中国大量进口丝绸、瓷器等产品。
正是因为这种较强的生产生活用品的经济能力,中国人口从乾隆中期的约2亿多上升为乾隆后期的3亿多。乾隆时《吴县志》记载,“国家太平日久,人民户口百倍于前。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搏,山无不采之木石”。可见其经济之繁荣。
另一个认为乾隆朝乃“盛世”的原因是所谓当时国库充盈。在清康熙四十五年、四十六年时,清朝国库白银存量超过5000万两,到了雍正七年,库银有6000余万两,超过前代。而乾隆三十七年,户部银库存银“多至八千余万”,又超过了雍正朝,前代各君更加无法与之比较。并且,康雍乾三朝不是只有某一年库银多,其他年份却剧烈下降,而是国库充盈的时间很长,这在乾隆朝更为突出。有人认为存银突破8000万两标志着清朝到了极盛时期。
然而,乾隆时代中后期二次进剿仅有几万番民的大小金川之战就耗费白银7000万两,再加上后来的缅甸之战,还有征回部、征越南,每次国库都是开支巨大。从历史中我们看到:顺治时代八旗子弟的打仗不需要用钱,大清初期也没钱;康熙时代也有场面很大的战争,那时打仗并不要花费如此之巨;而乾隆时代的花费相对巨大,乾隆末期和嘉庆初年的一个白莲教之乱,就使清国库出现亏损,因为那是一个仿佛没有钱就打不了仗办不了事的年代。所以我们仔细分析:乾隆国库那点钱是比前代多,但真不足以作为国力强的根据来提出。不仅如此,如果用人均概念来衡量乾隆国库的话,还不如前代。
乾隆时代受到追捧的原因在于大家对于经济的看法,对钱的盲目崇拜,是羡慕那个时代有钱。人们很肤浅地将钱多与国力强混为一谈。
对于乾隆时期的英国人来说,日子真是不那么好过。在北美战争的失利不仅使英国失去了美国这个巨大的殖民地,而且使英国政府债台高筑。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并希望从中获利,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借给乾隆皇帝祝80大寿的机会,派遣特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副使斯当东率领军事地图绘制人员、情报搜集人员、秘书、医生、翻译及精通化学、天文、力学、航海等方面的专家、博士 100 多人(加上各船水手和其他工作人员,整个使团人数超过 850人)的庞大遣华使团,于1792年9月29日从朴次茅斯港出发,乘坐英国最先进的风动力战舰——狮子号,取道澳门开往天津。
应该说,马嘎尔尼此次访华除去炫耀英国的武力之外,更是一个军火和高科技产品演示活动。马嘎尔尼以礼物的名义带来了600箱包括新式榴弹炮、地球仪、自来火枪、英国最先进战舰的模型和望远镜等29种高科技含量和高军事价值的样品。马嘎尔尼本希望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观看英国军人演示火炮等新式武器,福康安却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想来没有什么希奇”。这次访华并没有给英国带来满意的结果。
当今很多学家经过测算:乾隆时代的中国比起美国的经济,GDP遥遥领先,照此说法,大清朝如何会在英国面前栽跟头?但世界公认:乾隆时代的英国是西方文明的象征,拥有强大的生产力,而拥有所谓巨大经济力的乾隆时代的中国却是停滞的时代。实际上很容易发现:大清朝和英国的经济内容并不一样。
大清朝主要是生活经济,而当时英国经济包含大量的国防经济。英国人瓦特1769年刚刚发明蒸汽机,大英帝国很快将其装到了战舰上面,从而使其战舰性能大大提高。并非之前的清朝不重视科技和军事装备,小小的清朝在与明朝的战争中迅速学会了火炮的铸造,康熙年间铸造火炮取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口径110毫米,重1.1吨,在当时世界上并不落后。康熙年间,对俄战争中清朝军队的武器也并没有太多落后,对台湾的进攻也证明了当时清朝具有相当强的海军能力。而在乾隆时代,清朝的国防经济几乎没有任何进步,仍然处在马刀、弓箭的时代。马嘎尔尼出使带来作为礼物的枪炮,也被随手丢在圆明园的一角,直到19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英国水兵才猛然发现:原来中国早就见识过我大英帝国的好枪好炮,但中国却不知道加以仿造发展。而当时中国的近邻日本也已经学会了火枪的制造,并早已在战争中大量使用。
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长时间的歌舞升平使人们产生了思想的变化。人们的目光更多地离开整体安全的保障,而更加注重自我的生活的舒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更多的生产集中到了生活舒适品和生活奢侈品上。当时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陶器、漆器、古董、药材、书籍等,不难看出,乾隆时代的经济只是生活经济,缺乏国防经济,没有重视国家安全产品生产。
当生活便利品和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能力已经成为经济的重要指标,我们误认为这个指标高就是经济状况好,而因此忽视了生活必需品和安生必需品的生产。
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济”一词,在中国古汉语里面是经邦、济民的意思。现代西方语言中的“经济”一词是economy,此词源于希腊语oikonomia,始见于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对经济的定义是“谋生的手段”。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观点就是要区分必需品与非生活必需品,他认为,包括耕种、捕鱼、打猎等能够提供人们生活必需品的活动才是要支持的经济内容,而那些获取超过自身需要的物品的活动则是需要反对的经济内容。我们不得不佩服两千多年前这位学者的真知灼见,他告诉我们,经济的本质在于必需品经济。
历史证明,超出必需品范围的过多的生活经济不会对国力增长有帮助。1840年开始,中国仍然为富人们生产大量的生活便利品和奢侈品,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那些便利品和奢侈品的生产能力根本没有用,大清显现出来的是如此软弱。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国还是几乎没有自己的国防工业,花费巨额金钱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北洋水师徒有其表,世界都不会相信偌大的中国竟然在甲午战争中败给土地面积和所谓经济实力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比的东亚小国日本。
那些雕梁画柱的渠家大院、韩家大院、马家大院等等,那些大清奢侈腐败的标记在今天被整葺一新,供现代人来顶礼膜拜,并将这种奢侈作为富裕的象征。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一桌的晚宴、几百平方米的住宅,这些又重新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对奢侈品的渴望是社会堕落的体现,因为这种过分的可以被称作贪婪的追求离开了人们真正的生命意义,使我们的发展充满危险。
当生活便利品和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能力已经成为经济的重要指标,我们误认为这个指标高就是经济状况好,而因此忽视生活必需品和安全必需品的生产。过多的生活便利品和奢侈品没有用,生活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增加不会增加国力,反倒会占去本来就非常有限的土地、能源、人力等资源,甚至会消磨人们的斗志。
我们不能被生活经济蒙住眼睛,也不能步乾隆时代的后尘。

北京故宫太和殿

2005年3月20日,杭州,一位大厨正在从一只直径达0.8米的瓷鼎里盛装炖了10多个小时的蛇龟汤

2007年9月4日,扬州怡庐食肆推出乾隆御宴,一位服务员正在展示别具一格的“乾隆菜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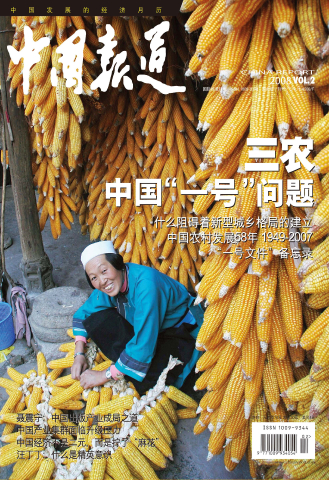
 Copy Reference
Copy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