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机制是一个事关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重大课题。

国有企业改革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经济难题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其中,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问题可谓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国有企业各种经济活动的决策者,经营者自身的经营能力与努力程度对国有企业的效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国有企业缺乏一种高效率的选拔机制,以至于往往无法将真正拥有经营能力的人才选拔到经营者的岗位上。因此,如何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机制是一个事关国有企业改革成败、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应当由谁来选拔国有企业的经营者
衡量一种选拔机制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是由这种机制所选拔出来的经营者能力的高低。由于能力本身是一种很难直接观察到的素质,因此具体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中,能够客观反映一位经营者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是在其经营之下的企业生产效率的好坏。问题在于,对经营者经营之下的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观察往往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而且这种方法类似于一种事后的检讨,顶多只能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无法事先对经营者的能力做出一个大致正确的判断,所以在一个崇尚效率与信息的商业社会中是没有市场的。因此要对经营者的能力进行较为有效的预测,还需要找到一种能够预先大致地反映经营者能力的指标。
目前,种种分析充分地显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机制是低效率的。低效率的根源就在于国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廉价投票权”和“道德风险”。要改变这种低效率的选拔机制,必须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使上述的两种权利统一起来从而消除“廉价投票权”和“道德风险”。因此,必须找到一种产权安排,使上述两种权利同时掌握在国有企业里的某种经济主体手中。简单地说,就是要使这种经济主体一方面拥有对企业经营者的选拔权(即剩余控制权);另一方面要通过某种分配机制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中得到利益并承担风险。只有这样,该经济主体才有能力并且有动力通过选拔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经营者来对企业的生产效率负责,才能杜绝“廉价投票权”与“道德风险”。
这种产权安排并非雾里看花,其实就是常说的股份制改革。简单地说就是由以拥有股票的方式享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组成董事会,以投票选拔经营者的方法来行使剩余控制权的一种制度安排。西方国家的大型公司多半采用这种制度安排,并通过经营业绩证明了这种产权安排的优越性。但是,在企业国有这一前提下,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实行股份制,国家自然是最大的股东。“国家”是指谁?是指全体人民,而一个企业的股权要分配给全体人民在实践中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来,作为最大股东的国家又成为了毫无意义的纯学术概念。理论上属于国家的股票仍然要通过委托——代理机制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仍然无法解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对称带来的“廉价投票权”与“道德风险”问题,只不过表现的形式由直接通过行政指派与命令来决定经营者,转变为通过实际操纵名义上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所有的股份来间接操纵经营者的选举罢了。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要找到现实存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股东来代替虚拟的“国家”统一掌握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决定国有企业的最终股东必须是国家,所以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股份制,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做些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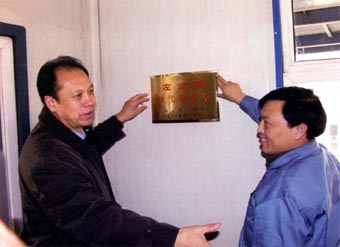
燕山石化举行职工创新成果冠名授牌仪式
笔者假期曾在河南省某国有汽车制造厂实习,其间关注过该厂正在试行的股份制改革:该厂根据工龄的长短和职位的高低,规定了从管理层到员工每个人各自可以持有的最高股份,然后让每个人出资购买股票,每个人可以购买的股票不能超过规定的最高额。然后由职位较高、工龄较长、持有股票较多的人组成董事会来选拔经营者。不但如此,该厂还规定,个人不可随意交易自己拥有的股份,只可以在企业内部职工之间交易,更严禁向企业外部投资者出卖股份。当企业管理人员或职工从企业“跳槽”或退休时,他所持有的股份必须全部返还给企业,企业这时按照当时的股票市价根据个人返还的股票总额以现金或其他报酬的方式给个人以补偿。而回收的股权再按照上文所述的机制出售给尚在企业工作的人员。
这种机制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将国家股份暂时“租借”给个人保管,再根据保管的好坏由国家向个人支付“租金”报酬的产权安排。其中个人购买国家拥有的股票的资金可看作是“押金”,而离开企业时国家支付给个人的补偿是押金与租金之和,其大小取决于经营效益的好坏。如果企业在此期间经营状况较好,股票自然会升值,购买企业股权的个人便可通过股票的升值获得比购买股票的资金更多的收益;反之,如果股票由于企业经营不善而贬值,购买股票的人便要承担由此而来的损失。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便以这种方式暂时掌握在了股东的手中,企业的利益由此与股东的利益紧密挂钩,作为股东自然有很强的动力选拔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的经营者。此时若将代表剩余控制权的选拔经营者的权利交给由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便统一在了股东的手中,实现了一致,从而解决了由这两种权利不一致带来的道德风险与廉价投票权问题。这时的选拔机制应当是高效率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或者说是产权安排能够在解决经营者选拔机制效率低下问题的同时保证企业的最终所有权仍掌握在国家的手中,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和长远利益。

如何将求职者引入风险机制
现在,已经解决了应当由“什么人”来选拔经营者才能使选拔机制高效率的问题。那么,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有一个真正关心企业的经营成绩、求贤若渴而不是各怀鬼胎、任人唯亲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在面对复杂的经理市场时,如何有效地识别真正具有经营能力的企业家?
在一个商业社会,任何理性的求职者都会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经营能力。在国有企业选拔经营者时,要通过产权改革使企业的经营成绩与经营者的个人利益紧密挂钩,简单地说就是要求经营者自己出资购买相当数量的企业股份,在经营者离开企业时,根据当时的股票市价向其支付现金。如果企业此时经营成绩较好,经营者便可从股票升值中得到红利,反之则要承担由股票贬值带来的亏损。这种产权安排的好处在于能够将拥有较多财产而对自己经营能力预期较低的人拒之门外。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当一个拥有较多财产的人决定当国有企业经营者时,他等于是在拿自己的财产进行一项风险投资,如果他对自己的经营能力预期较高,那么他也会预期在他的经营之下企业盈利的可能性较多且盈利幅度较大,他从股票升值中得到的预期收益将超出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预期收益;而企业由于他的无能而亏损以至股票贬值的可能性则较低,因此风险较低;反之则预期收益较少,还不如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预期收益大。在这种机制下,任何理性的富有者都只有在对自己的经营能力预期很高时才会应聘国有企业的经营者。
一定的产权安排成功地将对自己经营能力没有自信的富人拒之门外,但同时可能会剥夺有能力而无财产的人竞争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权利,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股票;而且由于该机制只能保证选拔上来的经营者仅仅对自己的经营能力预期高,不一定是真正有能力,所以仍然有可能让过于自信而又无能的人占据经营者的岗位,因而没有解决如何减少由于经营者的无能造成的损失的问题,因此必须再设计一种制度来弥补其不足:当董事会拟推选一位经营者,而这位经营者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企业的股份时,可由对这位经营者投赞成票的股东根据所投票数的比例将自己持有的一部分股份暂时转让给经营者持有,当经营者离任时,要将其持有的股票返还给股东,此时要保证他离任时返还给股东的股票总值不得低于他就任时的股票总值。如果离任时的股票市价高于就任时的股票市价,在其经营之下的升值部分归他自己所有;如果由于经营不善使企业亏损,股价下跌而导致离任时的股票市价低于就任时的股票市价,经营者必须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弥补这一差额。此时由于经营者的无能造成的损失便部分转嫁给了经营者个人,股东或者说是企业的净损失减少了。
这种制度安排能够保证即使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经营者对自己的经营能力也可以有较高的预期。通过上述的制度安排,求职者被引入了一种风险机制之中,只有当他预期在自己经营之下企业能够实现盈利时,理性的求职者才会应聘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如果由于自己的无能造成了亏损,按照前述的制度,经营者必须自己筹集资金来弥补这一损失,一个本来就没有多少财产的人不仅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更有可能就此沦为“债务奴隶”,一辈子只能为了还债而拼命工作,无法拥有任何私人财产,可以说这种惩罚是相当严厉的。所以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是富有的人,任何理性的求职者都不得不对应聘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三思而后行。因此这种制度能够在不歧视贫穷的应聘者的前提之下保证应聘者能够对自己的经营能力有着较高的预期。
能力弱化问题——对经营者经营能力的长期动态分析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两种变化:要么随着经营者经验的积累,对于企业情况了解的加深等因素不断得到强化;要么随着年龄增加,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知识结构逐渐过时等因素而不断弱化。因此,对经营者的能力不能仅仅进行短期、静态的分析,还应当进一步考虑在位经营者经营能力的变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衡量经营者能力是强化还是弱化了,最直接的标准就是看经营者经营之下企业的效益变化,如果效益逐渐变好,说明经营者的能力是不断强化的;反之则说明经营者的能力在弱化。而无论是强化还是弱化,经营者的能力都是随着经营者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可以将经营者年龄的增长视为反映其经营能力变化的重要指标。根据这样的分析,结合计量经济学的知识,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断:当经营者能力强化时,反映经营者能力变化的经营者的年龄的变化在统计上应当与企业效益的变化是正相关的;反之,若经营能力弱化,则年龄变化应当与企业效益的变化负相关。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的经营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其经营能力强化或弱化的概率都是大致相等的,并不因为所在企业国有还是私有而有明显的差别。据统计,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年龄对经营能力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私营企业存在某种机制,当在位的经营者能力弱化时,能够及时将他们从企业的经营者岗位上撤换下来,让能力强的人接手。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年龄在统计上与经营能力负相关,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机制,当在位的经营者能力弱化时,无法及时将他们从企业的经营者岗位上撤换下来,从而使能力弱的人一直赖在经营者的岗位上,以至于损害了企业的效益。
要解决这一难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分析企业的产权结构入手,尤其是企业的控制权,常常容易被疏漏。在传统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不对称的企业里,经营者不拥有充分的剩余索取权,却拥有包括剩余控制权在内的充分的企业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权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对经营者的报酬机制,即所谓的“控制权回报”。那么,这种“控制权”如何构成对经营者的回报呢?具体地说,在传统的产权界定不清、控制权与索取权不对称的国有企业里,由于制度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对企业经营者的报酬没有以让经营者持有股份的方式来与经营者的个人产权挂钩,而是采取了诸如实物补贴、在职消费和所谓“隐性收入”的形式进行。另外,在职的经营者还可以利用自己掌握企业决策权的便利来为自己的亲友办事或是介绍工作。以上种种便构成了所谓“控制权回报”。在控制权回报的安排下,“更强的能力得到更多的控制权,而更多的控制权为在位的经营者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麻烦的问题在于,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可能在他在位期间变弱,在位经营者的能力的弱化对于控制权回报机制是一种严重的挑战。悖论在于,由于“控制权回报”要求经营者必须在位,一旦不在位,经营者可以控制的企业资源将大大减少,因此控制权回报必将大打折扣;又因为不掌握“剩余索取权”,无法通过“剩余索取权”对因丧失了控制权而损失的利益进行补偿,因此能力弱化的经营者必将千方百计地赖在经营者的岗位上。
而私营企业的控制权与索取权都掌握在私营业主的手里,如果他的经营能力强,可以自己担任经营者;如果他的能力弱化了,则可以雇佣比他经营能力强的人来担任经营者,而他自己仍然可以通过剩余索取权从企业的经营利润在他人经营后提高的那部分来补偿由于丧失控制权带来的损失,所以私营企业能够保证在企业家能力弱化时及时地由能力强的人接手。
由上,笔者认为要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能力弱化之后仍然赖在经营者岗位上的问题,应当从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入手:建立一种将企业控制权与支付给经营者的回报分离的产权安排,使支付给经营者的回报与“剩余索取权”挂钩。因为控制权回报机制要求其受益人必须牢牢控制住企业才能享受控制权带来的利益,而剩余索取权的受益者则无须直接控制企业便可获利,所以当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经营者能力弱化时,他即使离开企业经营者的位子,也能享用他贡献给企业的剩余。我们固然不能脱离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状态,笼统地比较控制权回报机制与剩余索取权回报机制的优劣,但是,在经营者的能力弱化和可能消失的情况下,“剩余索取权”安排使经营者以往为企业所做的贡献可以得到一种独立于控制权的回报,而不必死死把住企业控制权不放,因此往往能更及时地让有能力的经营者接替无能的经营者。■


 Copy Reference
Copy Reference